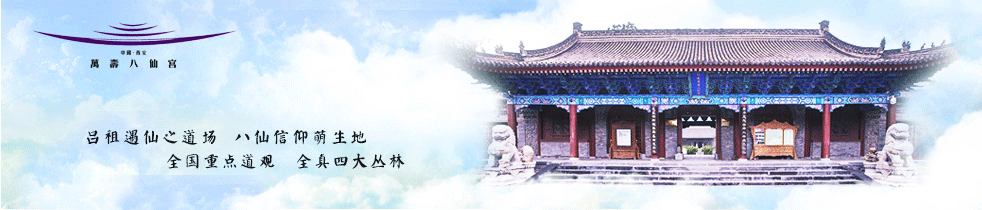《玄门道语》第三十五期:精神上的教益,托尔斯泰赞叹《道德经》
时间:2020-11-30 来源:八仙宫网络平台整理
作者:伊·谢·李谢维奇
老子,原名李耳,周朝末年人,圣诞为每年夏历的二月十五日。老子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伟大的哲学家,他曾仕周作过柱下史,学识渊博,后辞官入秦,著有传世之作《道德经》一书,又称《老子》。后世的道教奉老子为“道祖”、奉《老子》为圣经。
众所周知,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是最著名的俄国作家之一。每当涉及俄国小说家,那么通常与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和 契诃夫(Chekhov)并列在一起的就是他的名字。同样是众所周知的是,列夫·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个生活的导师,并且,他那在各个不同国度里都找到了追随者的学说一直到今天仍旧葆有它的生命力。但是,在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他对中国古典作家,首先是老子的了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却远不是人人都知道的。
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托尔斯泰的一个转折时期,是他的积极的精神探索形成其宗教——道德学说的一个时期。1877年,他同文学批评家H.H.斯特拉霍夫一起拜谒了著名的“奥普济那修道院”,他希望通过与那里的长老的交谈来使白己澄清思想中的许多困惑。但在当时,他对待基督教理论的态度已经相当随便了——他未能与僧侣们找到共同语言。正是在这个对托尔斯泰而言是不同寻常的时刻,当试图靠近正统的东正教失败之后,他接触到了老子的学说。
从H.H.斯特拉霍夫于1878年1月20日写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当时他在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工作,同时充当托尔斯泰寻检书籍的帮手——我们得知,他向作家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夭·茹利叶的法译本《道德经》的片断(见纪念版托尔斯泰全集第25卷第833页)。我们现在很难推断作家逐渐了解“中国智慧”的整个过程——用文献资料考证出的那几年对此也是显得不够的。但1884年确实是列夫·托尔斯泰发现古代中国思想家的一年;如果说在此以前,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他对他们所知甚少,那么,这会儿托尔斯泰手头有了中国著作家写作的西欧译本(主要是儒家和老子的著作),他惊叹于他们思想的深邃以及从内在精神上与他个人信仰的接近。
1884年2月,他在给挚友契尔特柯夫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在读儒家著作,这已是第二天了。难以想象,它们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精神高度。”(同前,第85卷第30页)在稍后的3月,他又写信给契尔特柯夫:“我正沉缅在中国的智慧之中。极想告诉您和大家这些书籍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教益。”而在3月15日,老子的名字与儒家一同出现了:“我认为我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由于阅读了儒家和老子的著作的缘故。”——他再一次致信契尔特柯夫,——就在这封信中,他首次提出了读者道德上的完善迫切需要划定专门的“读书范围”的想法。根据他的意见,这个“阅读范围”应当包括福音书、佛教典籍、罗马人马可、奥勒留和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著作,还有就是老子的著作(同前,第85卷第222页)。
不过,福音书在他所列举的书目中居于末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作家思想观点的演变。托尔斯泰继续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甚至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他如饥似渴地想占有所有人类所创造的、优秀的、最富道德意义的精神财富,他允许自己去干作为基督徒所不能容忍的事:他将多神教(偶像崇拜)的著作与作为上帝启示的福音书同等看待,甚至:他以前者去补充后者。1884年4月10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读了儒家著作,它们更深刻、更优秀(显然,这是与他所熟悉的欧洲作家相比——作者注)。没有儒家和老子,福音书便是不完全的。而如果没有福音书,儒家学说也就没有意义。”
可见,作家是如此醉心于老子和儒家的智慧,他希望通过东方文化来理解西方文化和通过西方文化来理解东方文化的愿望十分强烈。当然,托尔斯泰首先是从基督教出发去涉猎儒家和老子的学说的,因为他深信,“老子学说的实质与基督教是相通的。”他总是认为,所有伟大宗教的基础都是被人类心灵所证实的同一个神圣真理,只是由于这些宗教产生的年代与地点的不同才使这同一个神圣真理变得模糊了(见托尔斯泰于1910年2月24日写给B.A.波莎的一封信。同前,第85卷第374页)。老子著作中对托尔斯泰最有吸引力的是老子那深刻的精神以及他对这个世界上的“诱惑”的拒斥态度。
通过比较老子有关道的学说和基督教的学说,托尔斯泰认为,“两者的实质都是以禁欲方式显示出来的构成人类生活基础的神圣的精神因素。”“因此,为使人类的生活不成为苦难而能成为一种福祉,人就应当学会不为物欲而为精神而生活。这也正是老耽所教导的。”(同前,第40卷,第350一351页)托尔斯泰认为,“道”这个字既是God的标志,同时又是通向God的道路。他从中发现了与基督教学说直接的相通:“God就是爱”,而去爱别人正是通向理解God的道路(同前,第25卷第351页)。我(作者)为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解释感到担心,——一个明显的理由就是,人们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托尔斯泰从比较角度去处理的是他全然陌生的文化材料,对这种对属于极为相异的信仰传统的神圣文本所进行的文化比较能使作家如此成功地克服语言障碍从而深入到文本的实质中去,我们唯有表示惊叹。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1884年,托尔斯泰曾第一次尝试将《老子》译成俄语。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由教士丹尼尔·席维洛夫翻译的《道德经》全文已经在俄国外交部的档案中存放了几乎半个世纪之久了。托尔斯泰痛感俄国读者对中国思想宝库一无所知,他试图来填补这项空白。他写了三篇短文,并冠以“中国智慧”的总标题:《儒家的书》《伟大的学说》《中国哲人老子撰写的道路与真理之书》。这在他生前没有发表,原因也许在于作家本人意识到文章写得有些幼稚、也必定是肤浅的。从托尔斯泰所选译的老子名言中可以看出他对老子学说的理解:开头部分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认为的讲述难以言传的自然的名言;第二部分则全部取自老子的诗体名言(它被誉为“人类的慰安”)。
然而这仅是一个开头:托尔斯泰非常清楚,如果他真正打算更加深入地钻研中国哲人的作品,那么他所面临的工作量是巨大的。1886年7月,他急切地写信给契尔特柯夫:“除了我手头已一有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有关老子的书籍。”(同前,第85卷第370页)——他手头的材料不够。在这以前不久,作家便告诉他:“我不仅忙于研究佛教,还有婆罗门教、儒教和老子。”(同前,第85卷第356页)托尔斯泰感到良心受到了谴责,这是因为直到那时他仍未能编出供给人们进行富于教益的系列阅读所必备的书来,而对此他已经考虑好久了。“我早就读过许多可以并应当列入这套丛书的作品,”他在1888年写信给鲁沙诺夫时说,“我又早就具备了翻译和出版它们的可能性,但我却什么也没有去做。”
“我可以举出:儒家,老子……还有许多其他人的名字,但这些书的俄译本却一本也没有。”(同前,第62卷第152页)直到1893年,托尔斯泰终于同他的年轻助手波彼夫一道认真地来着手翻译《老子》了。工作进行得很不容易,时断时续,但它已经成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日常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一点可从托尔斯泰在9月份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清楚地看到。在信中,日常生活与富于崇高意味的精神劳动交织成一幅奇异的画面:“丹尼娅正忙于写信和动身前的准备,连画都不画了。孩子们去采集收获过的苹果园中的苹果……廖瓦好像胖了一些。E.и.波波夫在替我抄写手稿。我和他在重读和修改深刻的思想家老子的作品的译文,每一次我都怀着巨大的喜悦,聚精会神地去理解和用心地翻译,我是参照着法文译本和更加出色的德文译本工作的。”
再往下,他摘引了《老子》中的语句,并赞叹道:“这不是太美了?”(同前,第84卷第196一197页)可惜的是,当托尔斯泰的译文准备妥当时,1894年由一个日本人(丹尼尔·柯尼斯)用俄文翻译的《老子》却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后来又出了单行本。这个译本中有许多错讹,但显然,不懂中文的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无权与之争论。没有发表过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手稿还保存着。其中就有《道德经》的整个译本(不知为什么,其中少了第48和第49章)。另外有17大张写得满满的纸组成了这份手稿的第二部分,它的标题是:“列夫·托尔斯泰对老子《道德经》的解释。”
(本文作者为〔苏联〕伊·谢·李谢维奇(顾卫东译),原文名称《列夫·托尔斯泰与老子》,原刊于《国外文学》1991年第4期,第108—112页)
相关热词搜索:
分享到:
 收藏
收藏